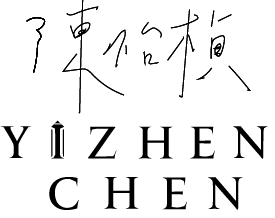2024/03/01
客語的每天,念作逐日(dag ngid)。慣習到可以反射性講出來,而偶然瞥見以客文寫作「逐日」,有點陌生、又有點熟悉。後來想想,覺得還真合適。
逐日,帶著能動性、不斷推進。然後之後還有然後,日頭升起又垂落,反覆輪迴看似徒勞無功(或許同時也是,毋須反駁)。
黑暗與光亮必定存在,運行軌跡裡的必然與和諧。
那就是每天。
1.
「應該是最後一次來這裡。」我心想。蹲在離原民宿最近館別的車道上,等候轉房的客人抵達。
我所待的民宿一大早就鬧水荒,開水龍頭沒水流。師傅一早就帶他看起來像高中生的兒子來檢修,但沒人知道馬達電源在哪。師傅中午就叫師傅的頭家來看,弄了一整天、太陽都下山,離去前,告訴我供應水源的馬達變頻器壞掉了,今天買不到零件、明天才能再來修。外頭臨海的公路上出了場車禍。
我說,頭家,安內挖無法度嘎挖人客交代耶……師傅跟我說,他說現在還是可以用水,他幫我們調整成熱水能正常使用,畢竟現在是冬天;冷水水壓就會比較小、高樓層的水壓又會比低樓層小。現場驗收完只好放他們走,公司群組回報,不然怎麼辦。
但果不其然還是出包囉。應急的零件在大量用水下被燒壞,客人電話一通一通來。
以前的自己,一定從早上就開始想問主管,如果今天修不好怎麼辦?是不是要提前先聯絡客人取消相關事宜?但他總說,怡楨,妳要相信師傅會修好。Jeremy要賺錢。
好的。這是Jeremy開的公司,不是怡楨開的。怡楨只能說,好的。
但出包了站在第一線被客人轟的總不是Jeremy、不是主管,是怡楨。去年八月排水孔事件第一次被客人罵哭。那時候還能哭,今天我彎著腰和客人說不好意思的時候,雙眼盯著地板磁磚的隙縫,壓根已流不出眼淚。剛才打給同事問他這一館的電視怎麼使用時還說,「欸,我他媽就算是硬擠、也擠不出眼淚了。」我開始笑。他聽起來像被吵醒的剛睡醒聲音,也跟著一起詭異呵呵笑。
後來學長趕到現場,滿身男用香水味,親暱對客人喊著記啊,拍謝啦,拍謝(其實我盡量不叫客人姐,姐什麼姐)。一起巡迴拍謝、教電視、問早餐時間,不斷跟嚼著檳榔的老8+9寒暄致歉,陪笑員怡楨只需站在旁邊漂漂亮亮地笑、跟著彎腰說拍謝。
時間來到23:02,結束巡迴。學長遞給我一根卡7,說陪他抽根冷靜煙。「怡楨,妳離職後我們到底該怎麼辦,我光想像就想自殺⋯⋯妳知道我剛剛是從火車站趕過來的嗎?我一聽到只有妳在扛,就馬上退票、飆車過來了⋯⋯抱歉,今天太多人休假才讓妳待到這種鬼時間。辛苦了。」想也知道,他會這樣劈裡啪啦道歉。
不想說沒事,只從他的後背拍了拍肩膀,說你也辛苦了。在我們背後的太平洋黑得要命,今晚沒有月光。
對了,我現在對在乎的人,與其說聲辛苦、較想祝福請早點休息。
回程只騎40。沒有唱歌、只是很冷。沒有想哭或委屈,只是騎車。紅燈停、綠燈行,看到二段要拐彎、行至白線前要停。回到家00:28去室友房間陽台收衣服,再出門騎車去辦公室,在黑暗裡敲著鍵盤作帳、放明細到抽屜,全都完成後再次回到家,01:04。一個人坐在高腳椅上吃無聊的便利商店微波食品,雙手環抱膝蓋還不小心睡著。我知道我沒熟睡,還聽得見室友在樓上洗澡的水流聲、以及自己發出的規律呼吸聲。自己在旁觀自己。
現在,我在火車上,拖著上班13小時、又睡不到一鐘頭的身體,再花時間鉅細靡遺地紀錄,的確像某種程度的自虐。但既然在坐車,我還是想給未來的自己看看,看看妳在即將24歲的這份工作與生活,有多荒唐。
○
我記得H說,當還有力氣說累,表示還沒有真的很累。
他也說,不滿意現狀就只有兩條路,一是嘗試改變體制、二是離開。
我們後來都選擇後者。我也是後來才知道,他24歲準備考研究所時,原來一直都沒辭職。我一直都以為他是全職考生,畢竟轉考的系所對他而言是全然陌生的領域。他會在下班後獨自騎去國家圖書館唸書,讀到十點自修室閉館、再回到無人的辦公室,讀到凌晨兩點再回家。隔天七點照樣起床去上班。日復一日。有天,一如往常停在中山南路等紅綠燈,大大的馬路上都沒有人,他說其實那天也沒有發生什麼事、也不是說特別累,但眼淚突然從眼眶溢出。「是用溢出來的。」他說,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。但視線越來越模糊,不得不趕快停到路邊白線掀開安全帽面罩,用手抹去滿面的鼻涕與眼淚。
他曾取笑我很久,妳這個拿書卷畢業的、還跟一群再在不分的8+9一起共事,未免也太蹧蹋自己了吧。他一講我就想到,跟我同年有讀研的朋友們,現在幾乎碩二,要寫完論文、準備口試了。而我在和一群荒唐沒文化只會用錢砸人的公司工作。每想到一次,還是會忍不住冷笑一聲。
本來收尾想停在清晨花蓮火車站後的山稜在初陽照耀下有多壯闊。但想想還是算了。的確漂亮,但是,我現在已站在高鐵月台,腳邊開始閃爍螢黃警示燈,列車即將進站。即將把妳運輸回家,嘴裡要堆滿新年快樂,堆滿疲憊的笑。
還是先讓我閉目養一下神吧。
我知道無法永遠深深睡去,但先讓我閉上一下眼睛吧。
2.
當我接過店員找的零錢、撈起櫃檯上四捆寬寬大大的封箱膠帶,才被樸實地黏醒,真快要離開了。
距離上次搬家是大學畢業。那時提前兩三個月列了一份「高雄再去一次清單」,不外乎就是喜歡的書店、咖啡廳、電影館,還有那條時常騎得悵惘的同盟二路、深夜喜歡晃蕩到無人的公園,蜷縮在塑膠溜滑梯的上頭,用手機獨自播放著王菲或張懸。窩在裡面有某種塑膠的悶臭味、還有午後沒有完全蒸發所殘留的積雨。夜鶯不時啾叫,空空洞洞、只覺得孤獨。人生總有某段時期會孤獨得令當時的自己難以忍受卻同時享受。花大把時間回溯和感傷,如隔層霧紗窗看花,花瓣上的露珠顯得更加寒美、空靈與朦朧。但每個場景、每個時分下所盛開(或來不及開就凋零)的花,大多很普通。
老友開玩笑說,已經可以想像我跟花蓮說再見的場面、會多麼滂沱、傾盆哭啼。我忍不住笑出聲而且無法辯駁。我確信我會流淚,我會傷感,我是如此重視機緣與感謝。只是這次已經沒有那麼多餘裕可以讓我好好告別。
離職當天,日日騎經的大橋施工還沒完成。對向車道掏空,臨時架起的綠色鐵網和紅色警示燈條靜靜懸掛。中間的路燈壞了,徒留一段黑。橋底的河水細流、卵石堆積,終會匯於不遠的大洋。我記得第一次騎在台11線上是第一次來花蓮看租屋,對於車程十分鐘的市郊竟如此荒涼,就能胡亂感動。如今,天天邊抽菸邊凝望太平洋,看著遊客面向大海,拍攝各種角度的照片。
海的顏色每天都在變化,山也是。
「花蓮再去一次清單」還沒列完,距離搬家只剩一星期。這次不刻意安排行程,只下意識地去買還想再吃一次的肉桂捲、再爬一次那座靜謐的山林步道,停好車,和旁邊老樟樹下搖著尾巴的黑狗說掰掰。如此而已。
但我相信在告別時仍會流淚。我必定會流淚。我並沒有成為一個不易感、情感不充沛的人。只是我沒有那麼多餘裕,去完完整整的回溯、去體會與對照初逢。歷經是輪胎壓過的痕跡,不一定都具特殊性──即使傷感,但釐清情緒的來源,就覺得沒那麼必要,徒手抹著眼周。
寫作也是,沒有像從前那麼多話想說。
大多讀者期待被感動、期待被精心設計或批判力道所打動。而我現在比較喜歡平平靜靜地看一場電影,沒什麼轉折或戲劇張力,它的魅力體現在夏日午後雷陣雨完的晴空裡,非常淡薄,空氣中殘著雨水的氣味。遠一點遠一點、冷一點冷一點,侯導的作品經常這麼說。
還是會流淚,但過了就過。微不足道,生命的本質大部分是一場空。
越來越少在平凡無奇的一天買花。不做計劃以外的事項。2024已經快過去六分之一但我還沒看任何一部電影。每個不知道我幾歲的廠商和同事,一聽到我真實年紀常會挑起高高的眉毛。超市買過多的蔬菜以為自己煮得完。餐廳點過多的食物但總吃不完。歌單越來越大眾。特殊性沒那麼重要。自我介紹已懶得介紹興趣。不要惹事。其實妳沒有妳想像中的那麼特別。
「我是除草工人,所知不多
還在黃昏的此處
就快完成我的工作」
——孫維民,〈除草工人的另一日〉。
請接受餘生沒有太多璀璨,逐日平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