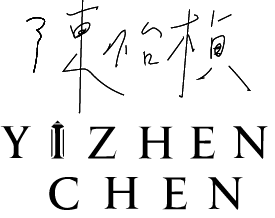2023/02/04
我爬到百年樓的大門口前停下。
在石階梯的後方,坐落一根根灰色的圓石柱。視線從柱底跟隨仰望,頂端至少也有三層樓高。其他人看可能不這麼想,但我就覺得像座殿堂、歷經風霜。比起上次假日來面試,大樓裡只聽得見飲水機嗡嗡作響的運轉聲、冷空氣凍得鼻頭發疼。而今天多了一些校園的味道,許多鞋跟摩擦、碰撞,不熟悉的低沉嗓音透過老音響傳遞,伴著些許幽微雜訊,迴盪於廊間。
我點開手機通知取回水瓶的信件,再次確認所辦的位置。四樓,我仍選擇走樓梯。因為不知道搭電梯要不要刷學生證。
然後,偷偷趁著走廊沒人,一手拿水瓶、一手舉手機,和所辦門口旁以篆體雕刻的研究所匾額自拍,想留下一點存在過的證明。
因為我怕這是我最後一次來這裡。
下山的時候雨仍未停。
路上沒什麼人,校內巴士從對向道路緩緩駛近,車頭燈閃著微弱黃光。地上的落葉被雨水打爛、形狀不完整。遠方的101被雲層遮掩、看不見頂端。水氣沾濕了眼鏡,世界逐漸變得模糊。我開始跌進自己的世界,幻想著只要不拿出學生證的話,毫無異議,我看起來就是這裡的學生──頂著一頭及肩的復古波紋捲、揹著如大石重的後背包、酒紅碎花古著襯衫再拖著燈芯絨褲、藍芽耳機一定塞在兩邊,管它到底有沒有在聽。
真是文青,別人經常這麼說。平常討厭這個字眼,現在暫時妥協。
雨天的顏色是以單調黑白灰所構成,在這樣無人的山坡路上,一切好像越來越魔幻、與現實越來越抽離,感覺隨時會有殺人魔或無頭之人出現。
我想起那幅無頭之人的畫。
第一次看見那幅畫,是在大二的文概課。
教室裡瀰漫著昏沉欲睡的氣息,教授漫不經心地用投影機播放作品。那張畫裡只有一個無頭之人,穿著不知是馬褂還是襯衫的白衣。沒有背景,只有像是一團團各種顏色疊加的霧氣,橘紅帶灰黑、黑灰至蒼白。他的右手拎著深色的麻布袋,渾圓厚實,那沉甸甸的樣子看起來就像是袋裡裝著一顆頭顱。
當時沒認真聽教授講解了什麼,只覺得看起來有點殘忍。
到了大四,我的畢業專題是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非虛構寫作。在滿堆的文獻回顧中,偶然再次瞥見那張畫,才知道那是畫家替多年好友的小說所畫的封面。
「蜿蜒路途中的無聲傷痕──探討小說〈山路〉及畫作《山路》」
研究計畫延續專題,終於完成後,我在首頁新增空白頁,以標楷體十八字級打下標題。我想,這應是全計畫裡最自然而然、不必絞盡腦汁就流淌而出的文字。在冷冰僵硬的學術領域,少數能夠不必爬梳、緊咬文獻不放的地方,有一點小小的創作自主權。「取夠好的標題,也能吸引教授的眼睛一亮。」我記得在上週的讀書會裡有人這麼說。
若切割掉文本所蘊含的歷史議題,其實我本身也很喜歡爬山。我喜歡這樣彎彎曲曲的感覺,像是一場修行,磨練自我與身體。為了看見山頂的景色,可以吞下路途中的所有辛勞與疲憊,好像所有的苦痛能夠在抵達終點的剎那即化為烏有。雖不知山頂究竟是遍地盛開、花團錦簇,還是一片荒蕪。
可是,最終我仍看不見山頂的景色。
其他人常記不得我到底報了幾間研究所,其實也無妨,他人的善意與耐心總有極限。日子久了,來自學科書裡的教養慢慢剝落,但對於像是去了哪幾座山頭面試、那天有沒有下雨、穿了哪雙不適合爬山的皮鞋……瑣碎的事物,我記得特別清楚。
當然,包含放榜那天。
最後一個公布的學校位於關渡的妖山,藝術大學的放榜日總跟其他間不太一樣。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,我的筆電網頁介面老早停在系所首頁。但不敢下午三點一到就按下滑鼠右鍵重新整理頁面,無論最後結果是要開始去找北投的租屋、還是……還是……
我不敢去想。那是殘酷的宣判、冷靜的告示、沒有還轉的餘地。
無法改變的事實。
所以我跑去看14:40的電影,買完票後跟A說一聲就把手機關機。不想在途中接收到任何訊息,無論道賀或慰安。但手機在口袋裡好像在發燙,左側的大腿上方幾乎要隱形灼傷。儘管努力讓情緒進入劇情,但直到結束也沒掉下任何一滴淚。最後,等到Roll Card都播畢、影廳人員開始進場收拾垃圾,我才緩緩起身,一步一步走下階梯,踩在布幔上的步伐沒有聲音。
指尖因空調吹得太久,冰冷而發黏。我凝視著全黑的手機螢幕,保護貼中央橫豎一條巨大的裂痕。
開機。17:26。沒有任何一則A傳來的通知訊息。
那一刻,我就知道結果了。
●
後來,日子過得極慢,近乎於停滯。
我變得很常發呆。坐在租屋處的椅子上,雙臂環抱膝頭,兩顆眼珠子直直凝視著穿透落地窗的陽光,看著影子在磁磚上慢慢變長,延長到發霉的木箱、沒折的棉被、還有地毯上散落一地的書堆。最底下那本包著黑色書皮的台灣新文學史厚得像字典,燙銀的印刷字樣與金色的陽光殘影交疊在一起。有點刺眼。
經常不小心忘記時間的流逝,讓午後挪移至夜深,偶有一輛尖銳車聲呼嘯而來,刮破空間,再迅速奔離。現在回首,在那段空白的時間裡到底想些什麼呢?但,似乎是什麼也沒想,近乎於禪修。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抽離掉眼前事物所有延伸的寓意。
為什麼要把所有事物都賦予意義?
當我回過神,暑氣縈繞,我已經簽下在花蓮的一整年的租屋契約。
紅色印泥不小心沾染到食指,看起來像乾涸已久的血跡。
「妳幹嘛要去花蓮啊?」這是半年來最常被問的問題。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幾乎都這樣回答。
我也經常在花蓮的山間流連。爬山時,看著前方的路:偶爾筆直、偶爾彎曲,突然爬升變陡、又或平靜緩淡。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、我不知道前方的路會帶我到何地。我只是想安靜地欣賞自然的風景,體會海風的鹹味、觀察傍晚雨後的光影、靜靜注視著清晨的稻子上停著小小、小小的露珠。
「那天清晨我本來要去自殺的,但最後我帶了一堆桑椹回來。甚至我的太太還沒醒。去看看太陽升起、或是晚霞,多麼斑斕美麗。」
這來自我今年第二喜歡的電影,是位伊朗導演的作品《櫻桃的滋味》,老人最後對男主角說的話。而他大部分時間面無表情地開著車,沒有方向、盤旋在一座座黃土沙堆的山路中。而我也一直遊蕩於山路,即使研究計畫和畢業專題早已結束,我仍在那蜿蜒的路途中迴繞、盤旋,已經不奢望能窺見山頂的風景,只偶爾幻想著無頭之人什麼時候要出現。
真希望自己也變成沒有頭腦和記憶的人,可是好像還沒辦法。
像是總會記得我在花蓮爬的第一座山是佐倉,來回約八公里、海拔高度不超過五百公尺。下午四點我往上爬時,許多人逆向行經我,他們已在回程。但我就想看夕陽。即使從未去過,但仍想像著綻放著整片的橘紅晚霞,會是多麼斑斕而盛大。但是,才爬到第三觀景台時,原本稍微露臉的陽光已消失在灰霧的雲層中。我站觀景台的二樓,望向前方一片霧濛濛的太平洋,沒有暖意光線的蹤影,徒留一片灰霧、冷色調的遠方。
這樣的場景,不小心,又觸動了一直壓制、迴避的記憶。這段日子以來,碎片如鬼魅糾纏,即使是再細微的場景或符號,只要一勾動,身體好像會自行起連鎖反應──點燃身體深處的未爆彈,血液如被滲了鉛,混濁又苦澀。接著迅速從頭頂流竄,到咽喉、胸腔、下腹、骨盆、膝關節、腳跟與趾頭,侵蝕至身體裡每一細胞和角落。可是彈藥並沒有一次爆裂就結束了,它仍沒有炸開,只任憑苦味與痛感無限伸張。躲在廣大無邊的大自然裡,但只有內心深處的自己明白,某些部份好像無法修復了。
但是,我也不確定那是永久性的傷口、還是沒有想要擦藥和包紮的念頭。
幾個星期前,在網路上跟陌生人聊天,因是匿名,所以不負責任地大肆傾瀉生活的絕望,「妳只是在享受咀嚼痛苦的味道。」他最後離開聊天室前丟下這句話;還有在上週給社團老師看散文初稿,讀畢,他停頓了一會,以低沉而溫和的聲音說:經營的細節、說話的口氣都很好、也挑剔不出什麼剪不乾淨的句子──只是,我看不見「然後呢」?
「我感覺妳就像是一直不去面對,這個巨大的否定就不會降臨。」
他這麼說的時候我不覺得被冒犯,反而和當週跟醫生討論的癥結點正好吻合──我習慣一直把情緒擱在一旁、迴避、不去處理,好像就能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。放縱自己在蜿蜒的山路中徘徊、不必前進。我以為我已經真正放棄看見山頂的景色了,但滑臉書時突然跳出那幾間研究所推甄的廣告,年份已變成112年,還是將文宣的每一個字仔細看完,也默背下報名的截止日期──
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四號。
或許是因忙於現今必要的日常公事苦勞、又或就只是沒有勇氣,最後我仍沒有再次報名。只是將那天額外空下,在太陽還沒出來的時候,去爬第二次的佐倉。
上次來爬是盛暑時節,即使穿無袖背心,仍汗流得渾身發黏。現則裹著厚重的羊毛圍巾,和兩條起了毛球的發熱褲。冬季的寒風打在兩側耳朵、後腦杓逐漸發痛,路上十分黑漆,我開著手電筒照明地面,乾燥的落葉劈劈啪啪地被踩碎。直到抵達大迴轉處的第三觀景台時,光線才真正充足了點。
我沒像上次爬到觀景台的二樓,佇於無人的第一層平台。我望向同一片山與海之間,沒找著太陽的所在,但四周已在明亮之下;太平洋一樣沒有盡頭,特別的是,海水的顏色竟有截然的分層。
淺藍至深靛。沒有漸層過度、分界很清楚。
不曉得那是洋流、還是其他深奧的海洋學識,只想好好拍照保存下來。我伸進口袋拿手機,打開螢幕,第一個跳出的通知是臉書今天有動態回顧。我開啟平台介面,跳出一年前的貼文。權限設定只限本人,照片上方有著淡淡的幾行字:
還是記錄一下好了
不知道明年的現在身在何方
我怕我是最後一次來這裡
下方照片裡的木頭篆體匾額氣勢依然磅礡、我的黑眼圈很深、左手拿著黑色的不銹鋼水壺,瓶底邊角因長年撞擊而凹陷變形。通常每年會在貼文留個言,作為歷年回顧。
我抬頭,望著遠方沒有盡頭、截然分明的太平洋。無聲的提醒。接著,不知怎麼地,我緩緩將食指移至貼文的右上方,點選功能鍵。
「這則貼文將被刪除,你也無法再找到這則貼文。如果你只是想變更部分內容可以編輯貼文。」
刪除。
重新整理,畫面空無一物。鼻腔突然掀起陣陣酸意,溫熱的液體從眼眶打轉。寒風持續拍打,乾枯無捲度的髮尾在胸前來回飄蕩。「好啦,好像真的該走了。」在蜿蜒的山路中徘徊許久,我仍不知道前方是何處。未知也無妨,只是在跨出新步伐之前,必須先決絕、正面的承認吧。不要再躲了。
觀景台上方阿公阿嬤的嘻笑聊天聲沒有間斷,方才的淚痕一下就被冷風吹乾。我深深吸一口氣,走出觀景台,往迴轉處的反方向繼續往上爬。
山頂應該就快要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