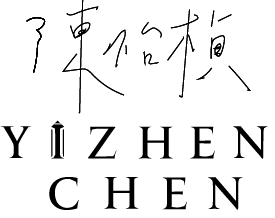2022/04/25
1.〈洞口徘徊〉
我張著眼睛,感受潮水穿梭。
來、回;來、回。
不知道現在幾點,沒帶手機,外頭天空沒有變明亮的痕跡。海聲拍附岩壁,拖著悶悶長音,慵懶、但凶猛。我赤著腳,雙膝拱起坐在涼亭周圍的長木椅。左臂趴在蓋骨上頭,隔著一層橄欖綠的長洋裝,寬寬鬆鬆,布料絲滑軟涼,如初的嬰孩肌膚,完好、乾淨。女生的皮膚摸起來應該就要像這樣,稚嫩甜滑、夏夜晚風裡的冰月亮,像小安一樣。左掌心不自覺用力抓緊膝蓋邊緣的布料,右無名指隨著中指滑進隧道。
淡淡的鹽味沾濕了髮梢,使髮絲結塊、變硬,搔癢光裸凸起的鎖骨。我低頭,看著稍微隆起的乳房不太規律地起伏,丘陵間汗濕了一塊。中指繼續穿梭於佈滿一顆顆小腫瘤的隧道,小心地滑。肉眼已適應沒有光源存在的黑,太平洋、蜘蛛蘭、小石塊,只要屬於自然原生物看起來彩度都很低,和諧的灰暗。只有涼亭外垂掛兩排螢光橘的救生衣暗中突兀。
忽然,有個摩擦砂石的腳步,輕輕輾過耳梢。
我迅速抽出,警覺地回頭,卻沒看到任何人影,聲音也消失。有點懷疑是不是幻聽。畢竟前幾天在差不多時間來月洞,也沒看到半隻野狗經過。雖然在開放時間之外偷跑進來好像不太好,但也沒有人在管吧──之前特地抬頭留意,林間走廊、乘船處、木造閣樓都有架設監視器──除了在洞口的涼亭。
即使空無,但突來的變奏,讓原本準備進入第二樂章的浪潮,乾巴巴地縮成一條休止符。
我低頭盯著併攏的兩指,濕濡的指腹裸露在空氣,敏銳感知尚未全然退去,細微感受幾秒之中迅速風乾指尖,徒留失去水氣的皮膚皺褶。像泡澡太久後皮膚乾巴巴的痕跡。
當時沒有發現,在我背後有一隻蝙蝠的屍體。
☾☽
第一次到月洞,不過也才兩星期前。
初夏正午,蟲聲縈繞,那時我在南石梯坪站牌下等車。螢幕顯示往成功的1145現在才到牛寮坑,也就是要再乾等半小時以上。忍受不了時間在原地消磨,於是開啟google地圖搜索:石梯坪才剛走完、海岸咖啡廳半小時很趕、南海的觀世音菩薩?有點無聊。
快要放棄想隨便走時,滑到月洞遊憩區。步行六分鐘。就這了。
到了月洞,我才發現原來不只是一個「洞穴」而已。往上爬了一小段階梯,一旁草海桐的葉片寬扁,因應海風慵懶搖擺。在三層樓高的林間走廊,竟發現還有苦楝枝枒的延長,剩下零星幾抹的淡紫小花。
導覽員阿麗看起來像我國小同學的媽媽,個子不高、肩膀與手臂相當寬厚,留著一頭長長的小波浪捲髮,髮量有些稀疏。她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是要穿救生衣才能進月洞搭船。放在涼亭旁的螢光橘救生衣聞起來沒有異味,只在幾個縫線處還是有一小點一小點的霉。
入月洞越深,線逐漸變少、地面越潮濕,但沒有海水的臭味;路程終點即乘船處,那已完全沒有自然光,需倚靠左右岩壁上頭的照明燈。
那船和我想像中的中型賞鯨船不同,類似於獨木舟,橫排只能左右各坐一人、中間再塞一個成年人勉強能走的狹窄走道。整體有點簡陋,照明也不大亮,但這樣增添了一點神祕、詭譎的氛圍。可能因為今天是平日,整艘八人座小船只有我、阿麗、和一個戴紅棕色宮廟帽的阿伯。阿麗請我跟阿伯坐到第一排的位子,並開啟放在船頭的銀色手電筒;而她則站在船身末端,拄著船槳緩緩開始划。
「歡迎你們來月洞,我是今天的導覽員阿麗。」阿麗說,聲調沒有什麼起伏。「月洞是全台灣唯一在半山腰的洞穴,也是唯一能划船進來的洞穴哦。這裡有很多天然的鐘乳石,你們有沒有看到左手邊這個石筍?就在左船邊下面,有人說這個石筍長得像關公。」我用手電筒直射,只見約三十公分的淡褐色長石柱,類似於臉的上半部沒有過多的雕刻,糊成一團。「這些鐘乳石都還是活的哦,大概十年才會長一公分。你們看右前方的縫縫,這是以前人為的切割,就被這樣破壞了,很可惜餒。然後前面拿燈的小姐請往正上方照。」我聽從,將手電筒往石壁上一晃,只見佈滿整片倒掛的黑體,有密集恐懼症應該會頭皮發麻。「這是台灣特有種哦,叫台灣葉鼻蝠。現在的數量還不算很多,冬天會是現在的三到五倍。現在蝙蝠正在睡覺,牠們晚上才會飛出去覓食,天亮再飛回來。」
我盯著這群倒掛的小傢伙,隨便目測,少說也有一百隻。
接著,船身駛向洞穴的盡頭。阿麗說,月洞裡的空間類似一個U字型,U的兩端目前被石壁擋住,後方仍有三十到五十公尺的空間,想過去只能潛水。船身慢慢轉向乘船處的方向划,我瞄了一眼手機,13:51,很好,還有足夠的時間悠哉走回公車站。
「對了,我剛剛忘記說,」阿麗突然提高了音量。「最早發現這邊的水源,是當地的原住民,就是我們阿美族啦。部落有傳說,如果以前有人得了皮膚病或痲瘋病、還是其他什麼傳染病,只要用月洞的水洗一洗,什麼病都會好。所以部落的人把月洞的水稱作『聖水』,也有『生命的泉源』的感覺啦。」
下船。外頭的天氣很好,陽光普照,從涼亭望出去的太平洋藍得很飽和,海面綴著銀色的閃爍。我解著救生衣的綁帶,隨口問了阿麗,為什麼月洞要叫「月」洞呢?是在洞裡看得到月亮嗎?
她微微皺了眉頭,雙臂交叉抱在前胸,兩顆斗大的黑眼珠往上飄移,看起來很認真思考,不知是不是太久沒人提出這個問題。
「照理來說,應該是要在洞裡看得到月亮啦,石頭跟石頭中間應該要有個縫隙之類的。」她用食指在空氣中比劃著,「但是喔,其實從我小時候到現在,月洞就是長現在這個樣子了。沒在月洞裡看見月亮過、也沒看過有什麼縫。」
我說是喔,順手將頭髮塞到耳後,左腕上的空心月亮被海風輕輕打著。
之後,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,喜歡跑到夜晚的月洞蹓躂。
起初只是帶著想知道晚上的月洞長什麼樣子的好奇,在洗完晚飯的餐盤後,便從租屋慢慢走二十分鐘到月洞。台11海岸線上,走路二十分鐘完全不算什麼。點到點之間的距離,經常都以小時來計算;且若尚未拋棄那雙都會的眼睛,這裡沒有全聯、沒有康是美、最近的一家7-11在豐濱市區,至少要騎十五分鐘的車才能抵達。的確,這裡就是個什麼也沒有的地方。
對我來說,什麼也沒有最好。
畢竟充斥太多理想,到頭來也是一場空。太緊、太快、太過頭。
大三休學是兩年前,搬到永和備考是一年前,去7-11寄店到店給小安最後一箱留在我這的衣服是一個月前。不對,還不到一個月。
逃來花蓮、或者是選擇豐濱,其實都沒有特別的理由,我已經不想要賦予所有的事情都有理由或意義了。不帶有目的,只是想像如果生活在山與海之間應該會很平靜。大自然或許是最後能包容我的安身之地。
小安會一聲不響地消失,我想像是一隻把浪浪養在房間太久,偶爾呼嚕蹭我、偶爾哈氣伸爪、偶爾又能在床上陪我睡到太陽升起。但在某個趁人熟睡的晚上,自己用前腳掌撥開紗窗、躍出玻璃,消失在無人經過的清晨巷弄,回歸自由。或許會有人說,為什麼當初不要加裝防護網,這樣她或許就不會離開了;但我總抱持著過度氾濫的浪漫──如果她真的喜歡跟我一起生活,我賭她就不會走。
所以自始至終,我都沒有對小安說,要不要當我女朋友。
房間遺留著為了貓所準備的沙盆、貓草與乾飼料,空氣中殘存淡淡的柑橘香;我以為把東西全都寄出、窗戶天天打開通風,就可以讓她的味道徹底消失在這三坪大的方籠子,但過了一星期還是完全沒改善。且又收到那封來自北投妖山的榜單,隔了一年還是看不到自己的名字被打成林○心印在上頭。
當天晚上傳了line給媽,說我要搬家。
去哪都好。不在台北都好。
最後決定住在這個房間,是在捷運上亂滑租屋網看見的。地區選擇花蓮、鄉鎮不限定,最新物件、重新整理──首張相片是張從窗戶拍出去的海面,陽光燦爛、浪花閃爍。真乾淨。
打了房東的電話號碼,隔天清晨就坐上首班新自強,下車後再轉乘客運前往;傍晚即在租屋契約按上紅指印,乾乾硬硬,有點像乾涸的血痕。
後來,因為衝著阿麗的那句「只要用月洞的水洗一洗什麼病都會好」,沒隔幾天就再去坐一次月洞的船。我特地帶罐空寶特瓶去偷裝。下船後,佇在涼亭裡仔細注視那瓶有點混濁的「聖水」。我不太迷信、沒有信仰,對算命星座運勢毫無興趣,就抱持好奇心與實驗精神,但內心深處又有點想死馬當活馬醫。
我扭開瓶蓋,緩緩地將聖水倒在左腕的月亮上。那是小安幫我刺的。
小安不是專業的刺青師,靠著設計系出身的繪畫功力,自己網購器材來玩玩而已。有次,房間暈染著黃光,結束後她趴在我的腹部,食指的指尖柔柔慢慢地在乳暈上繞圈,然後說想畫畫。她的聲音細到幾乎快聽不見。
「妳想畫什麼?」
「不知道。我只是想畫畫。」
我挪動身體坐正,盯著她的眼睛。她的下睫毛的很長,我輕輕地用嘴唇去碰。「那妳幫我刺青。」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很渾厚。
「要,這麼衝嗎?」
「還好吧,又不是第一次刺。」
「那妳想刺什麼。」
「嗯,」我停頓一下,腦海閃過許多平時存的認領圖:鐵鏽的鳥籠、簡潔線條的山海、陰影極深的煙霧繚繞……「我沒什麼特別想刺的,妳就畫妳想畫的。」
「好。不准事後抱怨哦。」她揚起一邊的嘴角,不懷好意地笑,拇指撫摸著我的手腕來回游移。她的指間末梢總是冰涼。
用「聖水」清洗後的第二天,我左腕上的月亮竟然真的消退了。
原本彎月尾處的尖端,線條正好接連到手腕動脈的邊緣;我不可置信地瞪著那條紫青血管,真的硬生生地跟黑色線條分隔出一條白膚空隙,就像整個月亮被人往旁邊挪了一點點。刺青的確有可能會過了一段時間後掉色或暈開,可是我那空心的彎月線條依然十分鋒利,沒有發散糊掉的痕跡。
於是當天晚上我再偷跑去月洞。在沒有光害的環境裡,肉眼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黑暗。雖然沒有要做什麼不好的事,但在非營業時間闖入,還是抬頭留意監視器,那粒圓圓的小紅點如血眼。我在心中算計著可被遮蔽物擋住的路線,而且現在的光源只有遠方微弱的月亮,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也不會拍得很清楚。售票亭旁的柵欄不高,且方格空隙很大,輕輕一蹬就能輕鬆翻過。
步行在夜晚無人的林間走廊,海風平緩。廊間右下方的太平洋柔和推動浪花,銀白色的月光反射於海面,在一片漆黑之中,那些細小的銀珠格外顯眼、閃閃發亮。今天的月亮渾圓飽滿,無懈可擊的圓。
我想起當時在小安刺完的幾天後,我問她為什麼不想畫圓滿的月亮,然後將剛烤好的酸種圓麵包切成兩半。小安沒說話,安靜地坐在胡桃木色的溫莎椅,盯著計時器走到2分58秒,再迅速將陶杯中的伯爵茶包取出。那專注的眼神,如一頭蒼鷹瞄準獵物,小小的腦袋裡精準計算著攻擊的時機。
「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。」她突然低低開口,一面拄著攪拌棒來回撞擊茶杯。
我盯著那黑色月牙,開口朝右、線條極細,框出一個彎月形狀,裡頭空心、沒有上色。曾經我極度熱愛為生活符號賦予意義,或許是備考生腦袋的連鎖反應──空心、不圓滿的月、刺青的原理即是在皮膚上製造傷口。
而這個傷口留下的疤痕,將會永恆烙印在身體裡。
☾☽
陽光斜曬,右臉頰如被蟲蟻輕輕啃嚙,不太會痛,但漸進將我的睡意慢慢拖離。即使未完全清醒,下意識第一個動作是抬起左腕檢查月亮末端的線條──嗯,和昨晚一樣。奇蹟或許只會出現一次、也或許是因為我手腕底下那條青紫色的管子,不是流著跟阿美族人一樣的血。
想不起昨晚在什麼時候睡著,畢竟沒帶手機。我伸手往背後撈,想拿脫掉的內褲,卻碰到一個冰冷僵硬的物體。
抽回手臂,如觸電的反射動作。儘管不和它接觸超過一秒,但瞬間讓我睡意全消。我想這個絕對不是木椅或石頭會有的觸感,稱不上軟,老化的彈性,如市場豬肉攤上某排不新鮮的腥紅死肉,按壓不會回彈。我的四肢都在木椅上,往前方的草叢爬。撿了片枯掉的草海桐葉。接著閉上雙眼,用嘴巴深吸一口氣──我要確保肺部充滿新鮮氣體,然後一鼓作氣、回頭、睜開眼睛。
出乎意料,沒有飄散著腥臭。牠的周圍很乾淨,身上沒看見任何傷口或血漬,但這絕不是睡著的樣子──
我眼前橫躺著一具蝙蝠屍體。
(待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