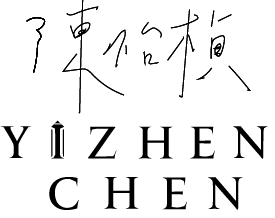2022/10/13
一回家,我看見H仰躺在客廳的地毯。單位是一攤。
「我、想不到、題目、要叫什麼。」她說得很慢、語氣平淡,眼睛望著天花板上的垂吊燈具,明顯沒有對焦。她繼續躺著,伸出手臂將茶几上未闔的筆電轉向我。
我盤腿坐下,在她的筆電稍微瀏覽:總共七張的分鏡圖,應該完全無字。首圖是一條捲好、整齊的皮帶,再來的分鏡是垂掛的燈具、沒有表情與五官的女子。接著是一連串「綑綁」的動作近景,只有皮帶與手,皮帶被繞成圓圈狀。在圖中昏暗的光線裡,似乎能預測到有什麼事件即將發生──後續的鏡頭逐漸拉遠,但女子只是將皮帶在褲頭上繫好、準備出門。最後只有一扇門,上頭的陰影極深。
「妳知道我也很不會想題目嗎?」我說。
「嗚……投稿截止只剩兩小時……」她無意識的摳著右手大拇指的皮。
「那這樣問好了,妳畫這些是想傳達什麼?」
「嗯,好難講……就是普通的一天,好像沒發生什麼事情,但也不是那麼簡單……我不想取一個很重或龐大的名字,因為它很輕描淡寫。」
「那……《皮帶》?或就《普通的一天》?」
「直接說破『普通的一天』好像又太直接了。」
「還是《繫》?」想到令我印象深刻的綑綁近景,但才說出口,自己也不滿意。太重了,也不是全篇都以「繫」的動作作為貫穿的主軸……
這時,L走下樓。
「欸幫忙來想題目啦,我們剛剛想了《皮帶》、《普通的一天》,還有《繫》。但感覺會有更好的。」她還在摳手皮,變成左手了。
「好哇。」他打開裝菸草的橘色鐵盒,邊捲邊看她的畫。他熟練的拿菸紙、菸草和濾嘴,動作快速而流暢、也不忘滾動滑鼠看畫。當他最後用舌頭舔舐菸紙作為密合,嘴巴還沒閉上前說:
「《準備》。」
空氣很安靜。
我沒辦法說些什麼。反正絕不是他想得很爛。一分鐘不到,邊捲菸邊思考、又能想到份量拿捏剛好的名字,很精準、不會太多:同時可以是「準備」迎向死亡、同時也能是個再普通不過的「準備」出門。我想到大二的油畫課,題目是早晨的天空。畫室充滿著亞麻仁油的味道,有些刺鼻。隨便瞄別人的畫架,大多是天藍、淡白、灰影、黃光……,顏料都堆疊得很厚,一直重複覆蓋。我也是。L的畫最後不意外地被貼在前方展示,「你們看,他的眼睛就看得到天空有粉紅色。要像他一樣,張開感官去感受顏色的存在啊!」教授滿是稱讚。
「其實我根本沒看到天空有粉紅色,我只是覺得加了比較不無聊。啊我們等等去吃弘記好不好?」在走回宿舍的路上,他滿不在乎地隨口說說。
從前我會很氣餒,關於那些不管再怎麼努力都追不到的才華和天份。我看著筆電旁的靛色陶器,沒有上釉、歪歪醜醜,裡面插著乾枯的綠繡球。那是我上星期在陶藝體驗課捏的作品。
「我覺得捏陶就是一直在經歷『妥協』的過程。」帶領我們的陶藝家說。
她長得很空靈漂亮,穿著無袖的大地色長洋裝、隨手紮到耳後的小馬尾映襯著白皙的脖子,身上散發著淡淡的木質調香味。聽說她其實原本念經濟系,後來自己太過茫然、沒有目標,就拋下一切逃來花蓮捏陶了。
「而且,其實我到現在都還不會使用拉坏機。比起追求一模一樣、相同規格的陶,我還是比較喜歡單純手捏陶土的感覺。雖然好像很普通、隨便一個人都能上手,但在平凡裡創作出一點點不平凡,這樣比較像我。」她脂粉未施,我好像能看見她眼睛深處的光。
後來,我也捏了一個很自己的陶。
跟一開始打算要做長柱體花器完全不同。從一開始在內心的堅持己見、到陸續一直塞新土補救,最後還是妥協、讓它順其自然的生長。
妥協之後,我仍沈浸在自己的世界:感受陶土冰涼柔軟的觸感、細膩地修補每一道細小的紋路和裂痕、傾斜弧度的彎曲程度,也思考著要如何傳遞原初想呈現的「原始」及「粗獷感」。後來撿了一旁地上的石頭,以它原生的紋路壓印,在那個像歪掉大碗公的花器內壁裡。
如今,它歪歪斜斜地站在茶几上、插著枯萎的花。有點粗糙、有點醜。
但站得很堅挺。
「幹…太強了吧……」H先開口,她沒在摳手皮了,現在用食指慢慢撫平剛剛摳起的死皮。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意識到自己一連串的動作。
「唉呦,他就藝術家嘛。」我語氣輕快。
「對啊,以後幫忙想名字我要收費。嗯……一次五十塊。」
「哥,很便宜喔。」
「沒差啦。我們去抽菸。」
我伸進的褲子右口袋拿那包快抽完的卡斯特,順手刁在嘴上、晶球沒咬破。一如往常,L走在最前面,打開大門。我突然停下,詳端這扇每天都經過、再普通不過的木色鐵門,意識原來這就是H畫中的那扇門。
但不知道是不是光線的關係,我覺得它的陰影沒有像畫中的那麼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