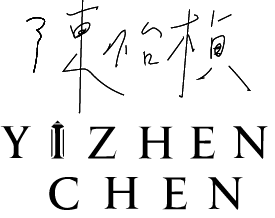2023/10/28
去年夏天我是用逃的,逃來花蓮。
大學一畢業,連滾帶爬從南方搬來東部。南方的陽光的確普照、燦爛得不得了,但好過頭了,那時不認為能值得這麼好,只想在簡單、容易居住的地方,山與海之間。沒有過多柏油路和人,取代路燈的是越來越稀少的木麻黃。但在那時候,我總無法簡潔地回答出為什麼要來花蓮。想必是自己也沒有想清楚、也還無法正視那塊考不上研究所、尚未癒合的傷口。但也管不了那麼多,只想逃。所以在去年初夏,陸陸續續瀏覽幾個租屋案件後,就乘著四小時的普悠瑪,搖搖晃晃來到花蓮。
我是在那時候第一次來到半寓的。在一口氣看完三間租屋的夏日午後。
不像一般咖啡廳為了容納更多組客人,把桌與桌排列得很緊密,把空間還給餘裕。大片的透明落地窗以深褐木框清淡包覆、不規則的鐵鏽工藝攀附於樑柱,一旁矮凳上的玻璃花器插著枯木枝條,沒有盛水。食器、杯皿不貪圖便利而大量採購相同的款式,每一件都是仔仔細細透過主理人那雙懂得觀美的眼睛,精心揀出的美感呈現與品味——來自阿美港口部落老頭目的黃藤編、日本陶藝家一顆一顆捏出的白瓷細珠小圓碟,又或在某場展覽中發掘到在地創作者所燒的灰奶土陶杯,所以買來用來日日喝水。在小小的一樓空間,容納來自各方的藝品或老件,共同展演歲月安好的歷練、靜默的和諧。
結帳時在櫃檯看到一盆從沒見過的花,白得乾淨、帶原始的奔放。細長花瓣如傘衣只剩骨架,花蕊纖細如絲、末梢垂著鵝蛋狀的橘紅,像殘留六隻腳、腳底沾染乾涸血漬的蜘蛛,野得張牙舞爪。我問這是什麼花,櫃檯的女子笑盈盈,說,它叫文殊蘭。她的眼睛笑得很漂亮,而眉心間有塊顯眼的疤,那兒膚色深了兩階。
後來開始居住在東部生活後,發現這種花並不難見。前份工作經常需去部落田調,帶我的S是位非常優雅有禮卻幹練的主管,說話總輕輕的。她二十幾年前在信義區做百貨精品業,後來才搬來花蓮。那時經常是S開著她車頭被撞凹的Honda,載我去豐濱的部落,必經之路為台11海岸線。我透著車窗,看見海岸線中間的分隔島上張著熟悉的舞爪。「怡楨妳看,」她單手握著方向盤、右手指著窗外,「等等去到貓公會有更多哦,連壁畫上也會有。」
「妳知不知道這是什麼花?」
隔年,換了份工作,巧得是都流連於同條海岸線。新單位的老闆也這麼問坐在副駕的我。不過他不是真的在乎,反而強調為何今天只開BMW而非保時捷,還說了兩遍。我親眼看過,他在荒涼的野地邊,將一株長得十分堅挺的姑婆芋毫不留情地一腳踩下,只因為,它稍微擋到了那塊標示土地所有權起始點的木樁。我漫不經心的應答著,視線放在外頭的太平洋,到了鹽寮時把車窗打開,想起今年還真的沒有舉辦海或了。每年的海或都說是最後一屆。
去年夏天初來花蓮、也是我第一次去海或。那時很想直接找現場的刺青師,不想刻意客製、而是尋覓緣分,如果找到喜歡的認領圖,即直接在踝骨上刺朵小小的花。但走了一整晚還是沒遇見。樂團現場彈奏迴盪、草味撲鼻遍地瀰漫,我以極慢的速度在市集邊緣,沿著石塊往海邊走。他人堆的營火燒得正旺,我躺在凹凸不平的石頭上,閉上眼睛,海浪聲猛烈地沖刷著感官,我靜靜地想,是不是還沒找到心之所向。
在心之所向、身之所往以前,是否必須先心知、才知所向?
到花蓮挖鑿了一整年,還是找不到究竟是什麼讓我如此挫敗、大費周章地逃來東部的原因。「不過就只是研究所沒考上,不是嗎?」付不起一小時2500的心理治療去追溯,就只能靠自己。
本就該靠自己。
好長一段時間寫不出來,也曾誤認正在步在攻頂的路上;而現在回首,那時陷於茫茫大霧,在霧裡的人不知身在霧中。即便踏出步伐,也不斷徘徊於蜿蜒,沒有前進,山頂並沒有快到了。那時產出的字頂多作書寫治療、稱不上作品。那你問我現在的字就稱得上好端端的作品了嗎?所動用的象徵與符號都緊密串連了嗎?敘事者的狀態不再停滯而繼續向前走了嗎?
當然沒有。但有意識地平穩行走,總比徘徊於霧中山路找解答,來得心服。
答案不在凌晨獨自與word對戰途中去院子抽菸時出現、也不在我大力翻攪著過往記憶,細細檢視殘存的碎片後浮出。而是在不寫的幾個月後、幾乎快忘了要找答案這件事的某個傍晚。那是個平凡無奇、剛吃飽晚飯,獨自沿著租屋附近的河堤散步,耳機隨機播出國中無名網誌的華語流行樂,一個制服皺巴巴的女生從我身旁經過,她側背書包太鼓、導致魔鬼氈無法吻合黏起;背影的肩膀一高一低,馬尾下方幾綹鬆脫束縛的髮絲垂在頸項,隨著走路的步伐輕輕晃動。
我盯著她,視線捨不得挪移;她的背影逐漸遠去、消失。我站在原地好久。
我好像是從國中會考落榜後,變成這樣的。
只將最後的成果視為一切。即便途中所獲再多,在最後抵達的校名之前,全不值一提。我想起那個滿臉痘痘、有著自然捲的小女生,因為只能走後門進私立高中而哭得那麼傷心,鼻頭擤到脫皮。國立、國立、國立,班導耳提面命,要考上國立人家才看得起妳。原以禁錮在考上大學後即鬆脫,但其實在成長時所受到的挫折,恐怕不是這麼輕易的離去。幽微、糾纏、陰魂不散。
我站在河堤,看著行道樹的光影、河面綴著路燈映透的黃,細細的粼粼波光,不停流動。很平靜。
沒有戲劇效果、沒有眼淚滂沱,沒有想立刻衝回家打開筆電敲入鍵盤記下。’讓它不著痕跡地淡淡寫過,也無妨。
後來,與其專注於是否走出、或為此產出多好的作品,此刻,還是比較想單純的生活──休假日午後,不外乎就窩在最喜歡的咖啡廳讀書,喝熱手沖、吃栗子焙茶戚風。公事LINE群關禁音、與待辦事項抽離,然後,靜靜浮現生活的本意。「你要有雙懂得觀美的眼睛」,日常軌道逐漸鋪成固定的形狀。看似百無聊賴,但生命的本質即是百無聊賴。日復一日的陳述裡,要在爛泥土中試圖挖掘一些晶瑩與剔透。即使到頭來發現是酒瓶的碎玻璃也無所謂。
我現在每天會穿過三個鄉鎮、會橫跨一條凹凸不平的顛簸大橋;在大洋的邊緣獨自駕著車、放聲地歌唱。每次扭緊油門加速時,已不覺是在逃。冬日海岸線的分隔島上不見殘留乾涸血漬的舞爪,想起今夏也沒在半寓看過它。若是從前沒到花蓮生活的自己,可能會因此客製一個文殊蘭刺在踝上,想富含文美、寓意、特殊性。但現在什麼都好、不知名的路邊野花也罷,順眼就好。別總再強加。
去年夏天,路途迢迢來到此地,即便拖著未癒之身,仍想問她、這是什麼花。不帶有目的或功利,單純對世界還保有好奇。
心知所向,就不畏遠方。到頭來也如此而已,我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