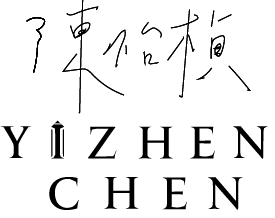2021/09/07
一弧鐮刀銀月高掛,映照在阿芬緊閉的眼上。濃密的睫毛盈滿淚珠,眼袋像埋了一條乳白大蟲般的浮腫,髮上添了好幾根白絲,她的面孔毫無血色,但仍令人覺得美麗。
她的床邊有一張破舊的小桌,上頭整齊擺放著一桶酸梅糖、三柱快燒盡的香,還有張泛黃的照片靜靜地倚在牆。她睡得不好,畢竟一整天的經歷令她精疲力盡。剛剛有做幾個短暫的夢,也充斥著猛烈的捶打或淒厲的哭聲,滿是苦痛與噩耗,卻掙脫不了,就像鬼壓床。此外,她今早的記憶也不斷重複播放,如同被詛咒、逃不出的禁錮──
她以為去殯儀館工作,就能在面對生命的離去時能夠從容不迫,所以她才想離開家去台北看看。而原以為已逐漸蛻變和成長,卻在今早七點看見那批推進來的大體中,有張面孔是再熟悉不過、和她同樣翹著高顴骨的那張臉……
她以為的蛻變和成長,馬上因那張臉而全然粉碎。
喪失平常扳起的冷漠臉孔,痛苦使她的五官嚴重扭曲。她不顧身旁的長官,忍不住前去握住他那隻蒼白冰冷、沒有血色的手指。她放聲哭泣,尖銳和痛苦似乎能透過聲音傳遞,一刀又一刀地刺入每個人的腦袋裡。
「聽說是她的三弟。」
「阿芬上台北後,似乎就和嘉義老家沒什麼聯絡。」
她被攙扶到生鏽的鐵椅上,整個人像是被吸乾魂魄一樣,聽不見旁人的耳語;且似乎一瞬間就衰頹下來、失去了生命的氣息,徒留一副空殼軀體──只差心臟還在吃力緩慢地跳動。她痛苦地閉上眼,誰也看不清她現在究竟在想些什麼,或許自己也是。
處於混亂之中沒辦法思考、也無法釐清下一步的去向是何處。
「疼痛可以使人清醒。」一個陌生的男聲從她身旁飄過。她緩緩睜開眼睛,分不清真實與幻覺。
「但在這殘忍的世間裏,還有什麼是真實?什麼是幻覺?」她喃喃自語著,空洞的眼睛不知該望向何方,地上遺落一張公司自家的廣告單正對著自己,「極樂殯儀館」五個大字更使人覺得異常悲涼。
下班後,她勉強拖著身體去巷口柑仔店買了一桶酸梅糖。老闆娘在結帳時打量她全身,納悶想著:「按怎今仔日歸个人攏總無了氣息?」
穿越迷宮般的老舊巷弄內,潮濕又陰暗。即使太陽還沒落下,仍一點光都透不進來。她在巷底前的木板隔間房前停下,而一旁的電線桿上貼著違章建築的紙張。
到家,她蹲在破舊的五斗櫃前,吃力拉開最底層的抽屜,小心翼翼抽出那張泛黃的照片。她很謹慎,害怕輕輕一碰就變成碎片。望著相片裡頭的人像,笑臉裡跟自己一樣的高顴骨臉頰……她忍不住跪倒在地,視線一片模糊,不小心弄倒桶糖,一顆顆從裡頭滾了出來,弄得亂七八糟。她已經喪失力氣去收拾一切,房內迴盪著她那發抖、瘖啞的哭喊聲───
「阿弟啊……阿姐買來你尚愛的糖仔了,緊轉來吶……」
強烈的捶打聲再次侵入她的腦袋,使她馬上從記憶裡回魂。那聲響彷彿那扇木門真被人猛烈敲擊。但驚醒之餘也無所作為,若不張開眼就不必面對一切。她覺得又是鬼壓床,因此放棄抵抗、任憑苦痛無止盡地蔓延至全身,「人會不會全然的喪失知覺?」她靜靜想。
「妳是吳勇的大姊嗎?」一個陌生的男聲再次輕輕傳來。那分不清真實與幻覺的聲音,和早上在殯儀館所聽到的好像。
「對。」她不自覺喃喃。聽到這令人熟悉又心碎的名字,兩道溫熱、濕潤的淚從緊閉的雙眼,滑落在毫無血色的臉龐上。
接著,她感覺到太陽穴被一枝冰冷槍口抵了住腦門。
隔日,火車站前大廣場中央照例立了看板。人潮眾多,照理說應該很喧鬧,但群眾們只瞪大了眼睛,沒什麼人說話。可能是立在廣場中央的看板,上頭的幾個血紅大字硬生生奪去了說話的能力。人們迫切地尋找自己所在乎的那些名字。有人跪地哭泣、有人昏厥過去、也有人鬆了一口氣。
在眾多人名之中,似乎無人在意看板上的最後一個名字。可能是不久前才寫下,因筆墨似乎尚未乾透。芬字尾端的那撇「刀」,仍在緩慢、無聲地流下鮮紅……
──獲2022高科大文學獎極短篇小說組第一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