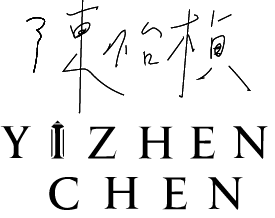2021/05/11
「好冷。似乎要刺透骨子裡的冷。」陽光尚未刺透的清晨。
雖脫離了太陽旗的統治,但太陽依然會升起,我們仍按表操課地日復一日。大家鬧烘烘地在早飯廳議論著阿芬的不告而別。我拄著下巴,專心嚼著無味的地瓜葉,與周遭似乎與世隔絕;但畢竟人耳無法自動收合、遇到那些無法接受的林林總總也沒辦法和眼珠子一樣視而不見。
「我們不是每天都在告別嗎?」心想,喝下最後一口菜湯。也是索然無味,死白的慘淡。
人們常在無法彌補時,只能透過幻想或諂媚來安自己的虧欠之心。經常燒著大把大把的金紙,卻在生前沒陪過一頓真心的晚飯。取叫「極樂」也是。但我其實已經厭倦思考或辯解這些了,除了把自己累死以外好像也沒別的可能。專心做好每天的柴米油鹽就已疲憊不已。
只是最近的忙碌實在有點過頭。
大概半年前吧,那時才剛來,即隱隱約約地感受到有些地方似乎不對勁。但又說不出口是何等的怪異。只是為何會如此規律、都在七點左右就剛好送進來呢。
每一天。都是。
「那個時辰是被下了咒嗎……」我用乾淨毛巾擦拭著蒼白的大體,眉頭間皺著困惑。盯著那一張張了無生氣的臉龐,總覺得祂們這些七點鐘被送進來的,長得都好像。我指的不是高矮胖瘦那類的相仿,而是感到一股遺憾、又有些無奈,或者是忿然……。從前,我也都認為每張死人臉長得都一樣;但這一年來,因為見到那不計其數、形形色色的人們,或許真能從那嘴角的皺紋、或是踝邊的傷痕裡,默默地分辨出因病或含冤地離去,有著何等的差異。
「好像想說些什麼,又說不出口。」我想。如果祂們能回答就好了。
好想問個明白。但人會說真話嗎?
我是指那些,活著的人。
雖然這麼想,但仍停在唇邊從未吐出。「耀善,你要記住啊。」母親虛弱的聲音回響在耳邊──「只要不關你的事情,就不要多管閒事。」她那雙哭腫的雙眼清晰、恐懼地烙在腦中。或許恐懼來自於那些穿著軍服、繃著臉、又說著一口外省腔的人們吧。空氣總是寒冷的,好像非得要把一切都刺穿開來。
照例的被推進來了,今天也特別多,二十三個。我想起阿芬,昨天她就是在這時候發瘋的。她尖銳的哭聲打破整個停屍間的死寂,緊緊握著被推進來的那個人,祂看起來相當年輕、應該不超過二十五歲。而阿芬平時那張最叫人癡迷的臉龐,瞬間和那根斷氣的指頭一樣慘白。
「聽說是她的三弟。」
「阿芬上台北後,好像就和嘉義老家沒什麼聯絡。」
議論的耳語嗡嗡作響,其實我真不太愛聽的。今天阿芬就沒來上班了,或許是再也不來了。
「動作快點!」那身穿軍服的老男人突然大聲喝斥,打斷了思緒。我換上應有的公事表情,提著桶子和濕毛巾快步向前。或許就是有這種人,現在的人們才會什麼都不敢問吧。和母親一樣。「打擾了,現在幫您潔身──」剎那,我倏然停下。手中毛巾無聲地落在冷冰的地板上。雙手的顫抖止不住。我直直瞪著那躺在我面前的男人,並且花盡全身的力氣來抑止震驚、說服自己──那個男人、並不是那張相片裡頭站在母親身旁的人、那個溫柔的挽著她的手的男人……「不是、不是!」我狠狠咬著下唇,血絲滲破皮肉。自我懂事以來就沒見過父親了。我閉上眼,在黑暗裏望向母親那哭腫的眼睛,那雙疲倦和恐懼交雜的眼睛。我從來都不曾問過、也不敢問──但是、但是──
好想問個明白。但人會說真話嗎?
我是指那些,活著的人。
淚水蠢蠢欲動地在眼眶打轉。我想起阿芬握著那根已斷氣的指頭。
「耀善,你要記住啊。」這時母親虛弱的聲音再度回響在耳邊──
「不要多管閒事。」
※備註:
極樂殯儀館,於1949年由日治時期臺北市役所經營的公營葬儀堂改建,為白色恐怖時期主要處理被槍決的政治犯大體之葬儀單位。原址位於林森公園新生北路二段與南京東立一段交接口處(今臺北市新生北路二段28巷)。
──獲2021高科大文學獎極短篇小說組第一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