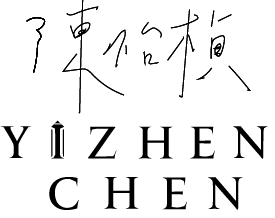2021/04/14
「如果不碰到封鎖,電車的進行是永遠不會斷的。封鎖了。搖鈴了。『叮玲玲玲玲玲,』每一個『玲』字是冷冷的一小點,一點一點連成一條虛線,切斷了時間與空間。」 ──張愛玲〈封鎖〉。
燥熱的人們悶著滿腔怨火,在這箱大烤爐中等待著耐心被慢慢地啃噬而盡;司機向乘客嚷著一會兒就好了,大概希望人們耐性多磨點。但,呂宗楨倒平靜得嚇人,只管掛著眼珠子盯著窗外,那永遠不透澈的台北天空。或許倒也不是上海的空氣比較清淨──明明那是生活在煙硝充斥與警報聲響的日子,但故鄉的一切總是比較美麗、沒有原因。
來這兒也好些時間了,但碰見公共汽車拋錨卻是頭一遭。從前的日子遇過幾回類似的事兒,只是少了太多的喧騰雜音與人聲鼎沸,所以總覺得稱台北是個大都會,恐怕是高估了些。他緩緩回頭望著車裏的人們,大家皆極盡所能地將能打發時間的法子,都給一一使了出來──有書的念書、沒書的就無聲地開合嘴唇,讀著車裏頭所出現的文字、還有的低著頭在摳摳捏捏著,似乎想在指甲和皮屑裡挖出些什麼、再沒辦法的就偷偷觀望著他人的偷偷觀望,還十分小心翼翼、好像生怕被發現。
不知怎地,他的嘴角竟微微上揚。因為這樣的光景感到有些熟悉。即使所處的城市不同,但人們在面對這種矛盾、似乎被凍結住的時間,所擁有對應方法也是一樣的無聊和瑣碎;但是,對於這樣的時刻,其實也並不全然的討厭。因為在這種介於真實與不真實的時空中,人們才可能有機會能逃脫出這座叢林──這座會將自我吞噬的都市叢林裡──好好地做一場夢。
他是明白這滋味的。他曾明白過。
翻開已脫了線頭的皮夾,裏頭嵌了張全家福相片。大女兒的酒窩深邃的對著鏡頭亮著,不禁勾起他的微笑、那是窩心又疲憊的。那年她才十三歲啊!沒想到才幾十年的光景,這成天哭著喊怕黑的小毛頭竟然也當了媽呀。但會讓那年的自己最想不透的,應該為董培芝最終還是成為他的女婿了。「唉。董培芝啊董培芝……真便宜你了!」邊笑邊碎念,他的眼睛拖出兩條深深的魚尾巴。明明先前那麼拼命地躲、想盡法子避開他,但最終仍是妥協了──不只向董培芝妥協、也向這樣的歲月與日子妥協、更向活了一年大半載的自己妥協。
他小心翼翼地抽出夾在全家福後的紙條。那是他還在華茂銀行當會計師的記帳簿子,非常緊急所撕下的一隅。上頭有著扭皺卻又被謹慎鋪平的痕跡,乾涸的墨漬因經年累月而暈出淚痕,但尚能讀出上面所寫的字跡。
天色慢慢被染成火燒的橘紅,而公車還是沒能發動前進。有位手捧著一疊英文考卷的年輕女教師,早已改完卷子而無聊得發慌。她長得很平凡、不特別難看──白白靜靜、像株剛盛開的純淨百合。她看見坐在斜左前方的男人捏著一張紙條發楞,側著臉的鼻頭暈著淡淡紅色。她感到納悶,原來這樣的男人──這樣頭髮已被灑了一層霜的大男人──還會在大庭廣眾前表露悲緒的啊?她好奇地伸長脖子,想看清楚那張紙。她猜,應該是個孩兒或女人的相片,好讓他有個念想、抑或有個心傷;還是那是張有些泛了黃、且不可告人的祕密情書呢?
「轟隆隆隆隆──」汽車的引擎終於啟動。它低沉卻又高昂的悶吼著,似乎巴不得提醒著人們該出發了。而那男人手中的紙,被這突如其來的吼聲震了下來,飄落至她前方的走道。她馬上就讀完上頭的字了,畢竟很短。但她在抬頭的那一剎,馬上與那正回頭撿拾紙條的男人四目交接。她窘極了,而且不用照鏡子也知道自己的臉龐一定脹紅得像顆飽滿的紅氣球。但那男人意外地向她說話──
「妳可以幫我讀出上面寫了什麼嗎?」他輕輕說。
「什麼?」她嚇了一跳。
「讀出上面的字。」
「七五三……六九……」
「再一次。語氣肯定一點。」
「七五三六九。」斬釘截鐵。她心想,今天可真是遇到了個大怪人。
公車終於緩緩起步往前,慢慢地帶著人們重新駛進那座叢林。但呂宗楨在車上大聲地笑了開懷,完全不顧其他人投來的詭異眼光。他真的已經好久沒笑得如此快樂、
如此真實了。
──致張愛玲〈封鎖〉、也送給R